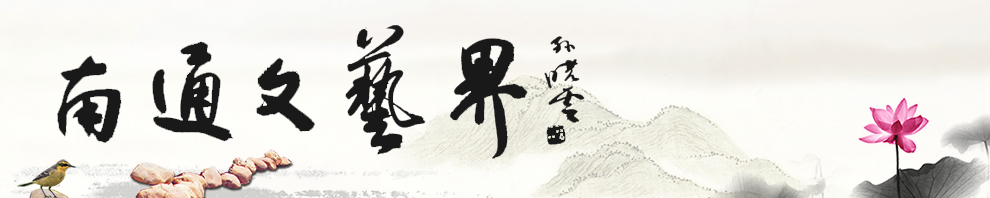文/翁剑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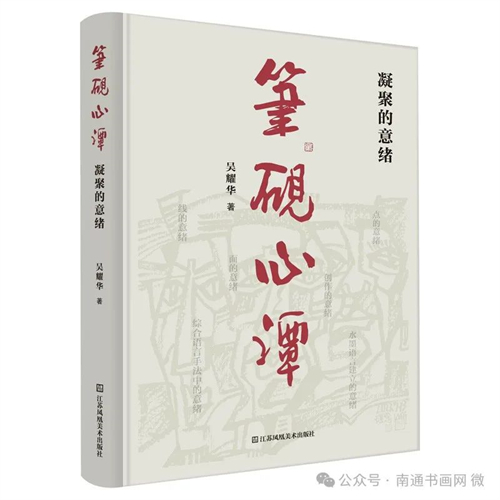
学友吴耀华近日寄来一本他的新作《笔砚心潭》,书中画作和心语交织并茂,视觉思维的美感意趣跃然书中,令人读来兴味连连。在我的感知里,吴耀华自大学时代至今绘画不止,笔耕不缀,是位十分勤勉并善于求进、求变的多产艺术家。他在绘画及相关理论上积累丰富,成果颇多。而今他把长期的绘画实践而生成的意向和心绪,集结成图文出版,成为他的艺术和教授生涯的又一重要果实和印记。吴耀华在此书中着重以他四十多年来对于绘画艺术形式语言的探索与创作心得加以理论性表述,其中以其异彩纷呈的装饰性绘画和彩墨画的形式意趣和多变的创作手法,向人们展现了他个人对于艺术实践和审美认知的诸多方面,以及画家个人丰富的心路历程。这对于艺术界的欣赏交流和对于后学者的启迪均有着可贵的价值意义。

首先使我感慨的是,当今国内对于艺术研究的一些写作,许多与艺术本身没有多少贴切的关联,较多是在一些概念和语言涵义上的阐释或对于文献资料的引用和发挥,而对于艺术自身特性及其生产方法与过程的深度发掘却往往欠缺。我以为其中一个方面在于理论者对于艺术本体和艺术实践缺乏应有的涉入和体验。然而,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艺术传统中撰写画学和画论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实践的画家,而非专职的理论家。在自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撰写美术史和理论的人士也多为艺术家或具有艺术实践经验的学者。(当然,出于知识领域和学科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以及研究目的不同而呈现的研究形态,可另当别论)。应该说,“艺术即经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是强调了艺术与人的行为和情感思维的直接作用下的成因,也是艺术家与特定生存环境相作用下形成的创作方式与方法。这不是一种纯粹的从概念到概念或从材料到技艺的生产过程,而是需要通过长期乃至无数的实践与思考过程的经验积累与归纳,方才成就了一个艺术家以及一个族类的艺术历史与认知。本书作者吴耀华的绘画过程和自我经验的累积和梳理,正是特定个体和特定时代的艺术过程中呈现的一个鲜明的音符与见证。

在吴耀华的《笔砚心潭》中可见,他在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的绘画中,十分喜爱运用装饰艺术的形式语言和手法进行以线造型布势并赋予想象的色彩关系。他的许多表现人物、青春、自然及近乎唯美性的装饰性绘画,显现出他早期造就的艺术学养与浪漫情怀。应该说这是一个特定时代及其美学思潮影响的使然。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语境下引入了西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艺术成果,如拉斐尔前派、维也纳分离派、纳比派、后期印象派及立体主义和野兽派等艺术流派及其美学主张被介绍到学院和社会;而当时国内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艺术机构为代表——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兴起的装饰艺术创作与教学实践的热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落成和传播,可作为中国现当代装饰艺术和公共艺术勃兴的标志性作品和著名艺术事件。其后的“云南画派”以及80-90年代各地的城市壁画潮流,均给改革开放初期被称为“文艺的春天”的繁花时节留下了诸多重要的艺术史实。如此艺术环境及美学新潮对于吴耀华的艺术思考和道路选择均有着重要的滋养与选择。一如他在书中提及的有关情形,此时期祝大年、袁运甫、袁运生、肖惠祥等一批著名艺术家的绘画对他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从他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现代装饰线描集》及其后的《中国画形式语言》,以及他研修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的过程中可以知道,他在艺术文化的现代化及国际化大环境下,对于艺术表现与审美的现代化、多元化和个性化形态的关切和长期摸索。以至于吴耀华在近40年来的绘画实践与学院教学的艺术长跑中,在装饰艺术和水墨画艺术的创作中始终在其形式语言和技法美学修养的日积月累、孜孜以求。其中在中西绘画经验的兼收和自身生活经验与艺术思考的并蓄之中,尤其在装饰性绘画和水墨画实践中均有许多显在的斩获和可喜的回报,实可谓自强不息,天道酬勤。难能可贵的是,吴耀华不仅善于作画还坚持理论性笔耕,以两条腿长跑的方式把艺术和学术性的果实呈现于社会,以实现其“独乐乐”亦“众乐乐”的艺术愿望。

实际上,在20世纪初以来中外艺术和设计界曾对于“装饰”的认识有过歧义或发难。曾有些人认为装饰注重外在形式上的修饰与美化,缺乏实用性或思想性;有的认为装饰艺术在重功能和效率以及直接反映现实方面几乎是多余的存在,也有的认为装饰不能为主题性、叙事性或宣传性活动服务,因而把它看作是次要的、陪衬的艺术。然而,稍有历史学、艺术史和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即可知晓,装饰艺术历来积淀了大量人类文化的内涵与美学经验,承载着不同文化历史中人类社会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情感,集形式与观念于一体,蔚为大观。可以说人类的艺术史即是一部饱含着装饰艺术的视觉经验和文化观念的历史。在进入现代艺术范畴下的装饰的传承与创造,其较大的缘由和价值意义在于“装饰”对于艺术形式自身的自觉性和纯粹性的历史性传承与现代性发展,从而对于后来的构成艺术、表现艺术、抽象艺术和景观艺术以及应用性的生活艺术均有着重要的现代性意涵。客观上看,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装饰艺术在绘画领域的兴起、历炼和再创造,对于中国的现当代艺术的形式语言的开拓和审美观念的现代性、自觉性和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贡献和长久的影响。
稍加回顾,装饰艺术的演化和发展在试图摆脱叙事性、再现性及说教性艺术而发挥不同个体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方面,曾带来异彩纷呈的艺术格局和累累成果。这在中国历代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和西方的古典艺术、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艺术和现代艺术的长河中,装饰艺术和含有装饰意味的艺术形式的人文与美学价值举不胜举。当然,装饰绘画和装饰性艺术并非就是“为形式而形式”的,更非仅仅是娇柔修饰的艺术,而是充满文化意味和创造性的多元化艺术。因为历史上人类的艺术都是具有某种涵义或文化意义的,装饰艺术或艺术的装饰性意义概莫例外。我们在吴耀华的《笔砚心潭》中看到他大量的装饰性绘画作品,显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艺术个性,包含着他观察事物和表现个人心绪的形式和手法。其中对于概略的抽象化的点、线、面、色等视觉元素的运用,呈现出他的审美态度和理想性图式之个案。此中可见吴耀华对于艺术的时代变革是十分敏感而身体力行的,这也自然折射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及其教育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形态的若干侧面,十分鲜活而生动。

如果说,艺术美感在于某种审美趣味和修养的话,那么在《笔砚心潭》中可见吴耀华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中对于线条、块面、色彩及其画面整体关系处理的长期推敲与磨砺,在于他对于表现对象、形式结构和视觉心理上的体味;其中西方现代绘画和东方传统绘画的经验均成为他的参照和养料,传统民间艺术的审美意趣和书法美学同样浸润着他的创作实验。同时他把对于现实生活形态的观察和体验作为形式与情感表达的重要依托,使得其作品与时代和观者的审美保持内在的契合。他善于把装饰性的形式及其构成方式与传统水墨画的表现加以新的融汇和组构,形成富有表现力的画面效果。其许多作品把装饰性与绘画性巧妙的予以结合,增添了艺术形式的丰富与生机、华滋与浑厚感,而把多余的细碎枝节加以剔除,使得画面意境趋于洗炼和整体性。他的诸多作品样貌,或繁或简,或虚或实,或严密或轻松抒情,均与画家在形式节律的对比和画面情绪的抑扬顿挫的把控能力密切相关。这恰恰需要艺术家的大量磨练和审美能力的养成,而非一日之功或概念上的坐而论道所能成就的。当然,画家在茫茫艺海和各种话语评论的影响下,需要坚韧持久的守住自我面貌且不断前行。艺术史中许多趋于成熟的艺术样式及风格大都存在一定的程式化、类型化问题,呈现出完备与停滞的矛盾性,需要艺术家予以面对和突破。艺术家永远是与自己“过不去”的人,更何况一部艺术史即是不断反叛与变革的历史呢。我想,吴耀华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遇到类似的情境。我想,他在《笔砚心潭》中对于自己的艺术和思考的展现,也是在寻求与观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探讨和对话的契机,可谓心之所致,意绪绵绵。
我以为,绘画艺术的欣赏,重在对于作品本身的观看和品味,而文字语言在艺术作品面前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因而,希望广大读者可以通过吴耀华的《笔砚心潭》一书和以往他展示过的诸多佳作,走进他的艺术世界和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笔砚心潭。
2024.7. 笔者写于北京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