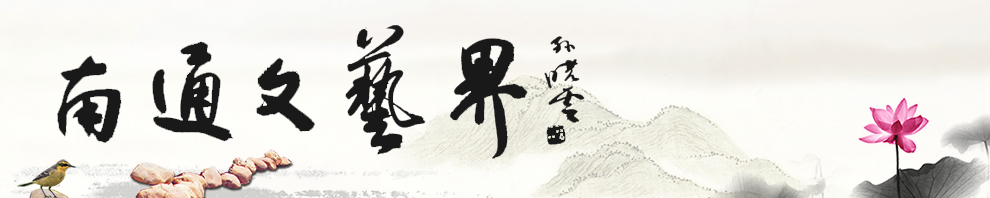一
“来在沪上的雨夜里/听街上汽车逝过/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打着柄杭州的油伞出去吧/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似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孟姜女寻夫到长城”
这是林庚写于三十年代的一首诗,作为一个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派诗人,那种“超越了古典浪漫式的感伤,而带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在诗里面不动声色地展露出来。这也是他自己所独立追求的“紧张机警”的自由诗风格。其实诗人应该是想克制自己的伤感的,然而那些诗的言词,已经不自觉地留下了种种蛛丝马迹,它留下隐秘的线索,诱导我们跟着诗人的目光去寻找,跟着他的足履踩在想象中的雨夜里——也许这就是诗人的另一种策略。毕竟,寻找,并且注定会失望与痛苦的宿命,对个人来说终究是种不堪。而借助诉说,诗人也让我们和那些纠缠他的怨痛迎面而遇。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压抑缓解了。于是,我们再也难以忘怀这段经历过的痛苦。
整首诗其实就是一场寻找的历程。诗人现身,一言不发,而我们只有跟随。于是,在那些不多的朴素的字句排列中,所有的一切都如电影镜头般,长短切换,将画面一一推至我们眼前。他想寻找什么?第一句“来在沪上的雨夜里”——“雨夜”,一个极富古典韵味的具体情境。对一个诗人来说,入夜,特别是风雨之夜,是咏怀抒情的大好时刻,“风雨夜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传统,在夜与思,激荡的风雨与澎湃的诗情之间确立了一种仿佛必然的联系。”一开始我们还准备好了一种闲适的期待,也许会听到一番吟咏。然而,他根本没给我们这个机会。因为他“告诉”我们:在这样富有情调的“雨夜”里,满眼看到的却是飞逝的汽车。本想寻找一种疏朗的情怀,却首先感受到密集的压抑。 一开始,诗人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一个有敌意的宇宙里的处境”。
然而,他还是想继续寻找。因为还不甘,还有些微的幻想。这又是一处转折。这首短诗中诗人暗藏的“然而”随处可见。尽管眼睛被汽车塞满,耳朵却还能听见雨漏声,是自己熟悉的高山流水般的音乐。这样的声响暂时缓解了诗人的焦虑,在他的下意识里,也许又涌起了一种近乎奢侈的念想:即使在上海,也能有让人心安下来的地方吧?于是,他出门去寻找——携带的,是杭州的油纸伞。几乎不用多说明,诗人自己就已经为我们画出了他的模样:眉宇间有抹不去的对传统或者是属于过往岁月的眷恋与牵挂。他带领我们出门了。
几乎,我们在他设置的这幕背景中就快要放松戒备了,也许不会再有冲突了吧?这两句是一个极富诱惑的招引,指示着我们走向一个想象中总觉得应该要出现的安详之地,那也是诗人心中所渴望的地方。但是没来由的 ,我们的心中还是感到隐隐的不安,因为我们清楚,这或者又是种伎俩,是一个甜蜜的陷阱。我们不确定下一个“然而”诗人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因为他总是不让我们安顿下来,因为他在焦灼,他必须得有陪同的人。他不允许我们有片刻的沉迷。
二
整首诗的上半段就像一个电影的长镜头,层叠的情绪掩藏在缓慢转移的镜头语言里,徐徐展开。而下半段的节奏却开始逐渐加快,他侧身,向我们做个邀请的姿势,一些画面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依旧是“现代”与“古典”各自经典意象的罗列对比——“柏油路”与“深巷”“小楼”“南胡”。而后者,会不会让你猛然有种时光倒流迷离惝恍的感觉?我们所熟悉的和这些情境纠结在一起的词句忽地就蹦了出来,或许是“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或许是“漠漠轻寒上小楼”?总之,我们的心在这一刻终于变得有些温润和柔软起来,那些融于我们生命的血液里的东西逐渐被唤醒,我们差一点就要沉醉于此了。但是诗人此刻在哪里?透过言词的烟雾,我们看到了他凝神细听的身影,然而,他的脸上却五味杂陈。他发现,在终于有些欣慰地觅到的深巷小楼中传出的南胡乐,竟然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曲声幽幽,画面暂且定格,不急,让我们也来聆听一把。
诗人终于开始忍不住表露了他的情绪——几乎是一种失望后的怨恨。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在凄清的城市雨夜里,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让一个青衫长袍的诗人心底乍然冒起的希望之火又旋即黯淡。他本来已经透露出了他的孤独——他面向着观众,诚恳地低声宣布:“现在我是,就这么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然而,却连一曲暖心的乐曲都不给他。我们在画外注视着他怨恨的面容,以为一切都快要结束,声光都开始减淡了。然而——这狡黠的诗人,他一转身,硬是让那曲南胡声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击中我们的耳膜——这居然是一曲“孟姜女寻夫到长城”!一切如同电影中的特写一样,没有任何装饰物了,就是那曲轰轰响着的“孟姜女寻夫到长城”无限夸张地奏着,拉过来,拉过去……
诗人不再多说了。一切都无需言语,音乐就是此刻流淌的内心。多少曾经缠绵的热烈的温暖的古旧的情怀都快要消失干净了,这就是他最终寻觅到的结果。其实一开始,他何尝不明白,这注定是一场痛苦的宿命。只是不亲自被打击便不会甘心。音乐笼罩着一切,震慑全场,让所有的人,包括画外的我们,无处可逃。
此时无声胜有声。诗人没办法再说下去了,“在他自己来说,除了在本来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地方停住不写之外,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的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然而,他最终还没有狠心到为自己设置一个无路可退的死角,他的态度终究还不是那么决绝,在他的心里,始终还有一个小小的善良而理想的念头:拉琴的人还是会有幽怨的吧?没错,就因为那个“似”字。其实,他原本可以选择一个全然否决的字眼,但是他没有。不是不能,只是不忍。在诗人的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十年后名震上海滩的那位著名才女张爱玲的影子,她说过,人世间没有那么多决绝的对立,她喜欢参差的对照。谴责中有同情,厌恶中有眷恋。而诗人林庚,也用一个“似”字有意无意表露了他沉默中的声音:这有敌意的世界里,还是会有些微的同情与爱恋的吧?
于是,在这首诗里,我们寻到了诗人那么多微妙而辗转的心境,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我们抛向他创设的那些情境,尤其诗的最后两句,是一个典型 的诗歌的“断片”形态。透过它,我们的注意力得以延续了先前的那些画面,并且在无法言说的沉默中,在无法逃避的诱惑中,一遍遍地聆听那一曲南胡——拉过来,拉过去, 苍凉沁骨。
(作者/周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