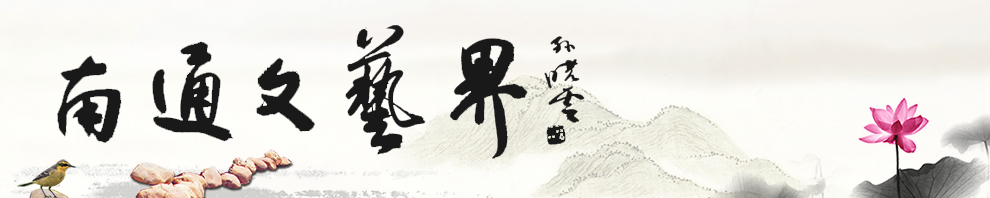《小先生》现在很热,很多人都在讨论由它带来的关于教育的反思。它当然对于教育有着深切的意义,但它首先应该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至少吸引我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文学审美质地。阅读过程中那种舒畅和愉悦,使我变成一个不大体面的人,常常捉住人就要谈谈这本书。
它的情感非常动人,笔法也很好,白描而淡泊。不浓,不烈,淡,但就是动人,有味道。比较中国,而且还正。老实说,现在很多剑走偏锋的写法了,走到狭窄一路上去,刻薄阴寒,要么就狂热,戏剧腔。弄了很多斜枝和梅花影子给人看,但你看不到枝干。《小先生》不一样,它也可算是一种正面冲锋的写法,一根梅花的大姿态几乎都能看到,虽然偶尔影绰了些。更多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个细节的特写,靠着这些特写,你的思想会开花。那些心上一疼,心头一暖,会心一笑,都来了,愉悦。
说《小先生》正面冲锋,其实是说方向,不是说力度。它不是拔剑弩张的冲锋,而是淡脾气的冲锋,方向是正的,力度是打太极。徐徐的,舒展,留白,温软,忽而一阵晚风过,恍惚枝头花已开。只呈现,不议论的。淡淡的白描,如画。芋头花,轻轻晃。
很讲究的语言,尤其注重名词和动词的使用,句式感性。好像庞余亮自己也说过,要用好名词和动词,如果把名词和动词都安置好,几乎就没别的词啥事儿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小先生》是一本用名词和动词写起来的书,也是一本用“句子”写出来的书。难道还有不用“句子”的书?不用这么奇怪,这里的“句子”是指文章里不经意间引用的当地口语。比如“栀子花,靠墙栽,雨不到,花不开,不信佛,吃长斋……”,又比如,把学生分成两类,“吃字的”和“不吃字的”。很多次,我想起了汪曾祺。《受戒》里的小英子,也是这么说明子的,她说他写的字,很“黑”。庞余亮应该是兴化人,和汪曾祺的老家高邮靠得很近,民风民俗乃至语言习惯,相互融化。汪曾祺也是不受句式拘束的,很多句子只有谓语,有的句子甚至只有排列的名词。花一样说开就开,长短句,名词。语言的风格上,庞余亮和他的苏中前辈一样,得了滋味。苏中平原出才子。
所以,如果你喜欢汪曾祺的小说,那么你一定也喜欢庞余亮的散文。其实我就是拿它当小说读的,《受戒》和《大淖记事》一样的小说。只是短些罢了。味道不变。难道不是吗?《小先生》虽然是一本散文集,写的却全是人物。这些人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学校里的校长,黑脸教导主任,等等,等等,甚至是庞余亮“自己”。各人各性格,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常常使人心上一动,会心一笑。庞余亮写人物,让我想起了归有光,寥寥几笔,传神,而又余味悠长。汪老肯定会高兴,家乡不远处的后生,写出了一本的的当当赓续且光耀了汪式审美的散文。
汪曾祺的作品里也有很多民俗风情的描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打开《小先生》,苏北水乡的气味扑面而来,余音袅袅中一帧帧展开的苏北风俗画,又在淡淡墨痕间,渐次隐去。
甚至连处理苦难的暖意也一样。汪曾祺的文字是褐色的,冬日暖阳一般照耀。庞余亮的文字是淡褐色的,芋头花一般轻轻摇曳。人生都是苦难的,看你处理的方式。庞余亮选择了淡泊的白描,也选择了用暖意包裹苦难。身体残疾不会骑自行车的学生,老婆摆糖担子的仇先生,父母双亲外出擒钱出了意外的孩子,因为狂犬病被家人打死的少年,真假公开课,民办教师转公,暑假在学校看书和孩子们烤知了吃的乐趣,竟然被误解成“好吃宝”,甚至是同事考研成功而带来的淡淡失落……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上下属关系,家长关系……人生里有不可避免的无奈和痛苦,人性里有难以回避的黑暗,这些都只是极少极少的斑点,庞余亮没有沉浸。淡淡的风吹着,暖暖的阳光照着,温柔的心软着,更多的光明和温暖笼罩着《小先生》,也笼罩着苏中平原上小先生们的人生。
我们敬爱的陶行知先生若是地下有知,看到《小先生》,恐怕会比汪曾祺更加高兴,睡着了笑醒了。因为这真的是一部乡村教育诗,献给二十世纪末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的教育童话。
这本书之所以被这么多的人热爱,除了它本身的文学品质非常到位之外,也因为它的情感非常高级,动人。当下很多自诩先锋的作品,都在刀尖向外,拔剑弩张,仿佛一日不愤怒便一日不先锋,一日不下作便一日不现代。何必呢?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内省。它是刀刃向内的。先把自己做做好再说。“攘外必先安内”。不要跟我说什么“真实”的重要。真实当然是重要的,不否认有一种真实,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当然会有动物的那一部分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人了,是人就要区别于动物地存在着,就要在动物的基础上继续进化,而不是退回到动物。这是生而为人的意义。烂就烂吧,没有谁不能接受,因为命运烂成这样谁都无法阻止。可是如果享受黑暗,故意摆烂,炫黑,就是令人作呕的。《小先生》的情感,高级就高级在不仅它的写法是内敛的,沉静的,它的情感也是内敛的,沉静的,一个自足的小宇宙,讴歌纯粹的师生情感和不带任何色彩的教育方式,带领读者享受温暖。
也许是都做过乡村小学教师这样一种相同的经历,《小先生》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心。这些似乎就是小先生这个人跟你拉拉家常、谈谈淡话儿的师生故事,实在是动人的。实在是契合着我的心路历程的,越看越感动的。《小先生》式的教育方式是非常艺术的教育方式,有时候,真的不必太在意课堂的纪律和秩序,容忍一时,待孩子们的注意力转移一下就可以,真没必要上纲上线对学生,睚眦必较。非常可惜的是,假使现时的老师还像《小先生》那样搞教育,怕不是要被批得一塌糊涂了,被下岗也是有可能的。校长一定会给你扣一个“管学生没本事“的大帽子。
多么动人的师生感情啊,都没了。我想我自己,就算这会儿还在做老师,还在乡村做老师,也做不成《小先生》那样的老师了。不可否认,人心的嘈杂和功利,把先生和孩子们的关系不纯粹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了。雪不再下,“乡下”其实早就没有了。时代配不上纯粹诗性的小先生了。怎不令人惆怅。惟其如此,《小先生》的存在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它是一首献给乡村教育的抒情诗,更是一首献给乡村教育的哀歌。悼念那渐行渐远的纯粹时代。也许还存在着一种唤醒,时代呼唤《小先生》式的小先生,小先生们也在呼唤一个《小先生》式的时代。教育真的是一种是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三方奔赴,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家长,有什么样的家长,便有什么样的小先生。说句不讨喜的话,“惩戒”本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惩戒是一种教育的艺术,没有了惩戒的教育,如同泥底的金杯,是不牢靠的。可是现在,你“惩戒”了试试,家长早把你搞到教育局,转眼之间你就倒霉了。
无论如何,感谢庞余亮先生。手捧《小先生》,使我温柔地疼痛着回到了上世纪末的小先生岁月,历历在目,且读且疼。曾经我也是有矿的人啊。我的矿,还没有挖,种种的因缘际会,就这样被我放弃。
怀念曾经的小先生岁月,致敬那些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仍然心怀光芒的人们。相信我留守教育的同学们都是很好的小先生,即使在教育并非塑造和唤醒,似乎只剩筛选和分层的当下,我仍然相信他们内心怀有的光芒。《小先生》这样的散文,难道会比小说差?所以说体裁只是借口,读者自有分寸,经典会自己在迷雾里发光。
(作者/低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