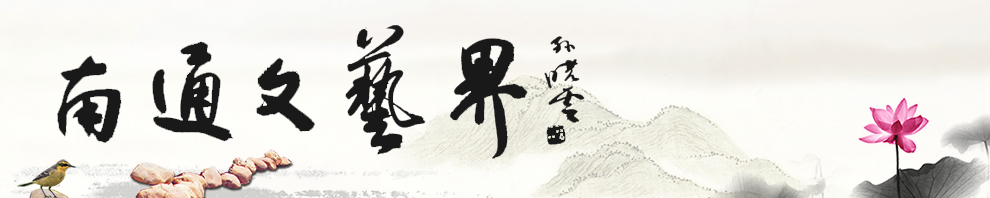优秀的儿童小说既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也能吸引和感动成人,储成剑的儿童小说《少年将要远行》就做到了这一点。解读《少年将要远行》要先从储成剑的文集《若即若离》开始。《若即若离》出版于2010年,收录了储成剑多年创作的小说及随感、时评等散文。作者在后记中说自己“与文学结缘也有二十余年了”,可以判断他文学成熟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是后冷战与全球化开启的时代,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属于两个世纪之间承前启后的十年。学者易晖认为,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一段历史陈迹,“但九十年代仍然内在于我们当下,我们仍然处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今天,无论是世界格局、国家发展阶段还是现实文化潮流,与九十年代相比都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他提出“九十年代化”的概念,用以指称这种延续发展的面貌。“九十年代化”摆脱了十年一个年代的时间禁锢,可以从1990年延长至新世纪,提供了一个更准确考察思想、文化及文学延展流变的视野。对于大部分70后来说,90年代是他们的大好年华,或是青春飞扬时期,或是成熟发展时期。他们见证和亲历了国家的经济起飞、思想的变革转型与物质的不断丰厚。他们在新世纪的步履,很大程度上延续自90年代的起步。在文集《若即若离》里,可以看到一位70后农家学子如何成长为医生、作家的努力,梳理出作者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程,了解到他对城乡变化、人情冷暖的观察,及当时的思考与心迹。在这个意义上说,《若即若离》是70后作家记录“九十年代化”的样本。
当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的思想、新的认知、新的技术不断生成浮现壮大,“九十年代化”逐渐开始远去。至于“九十年代化”何时明显远去,诸多学者将这个时间节点指向于2008年。那一年,汶川地震、奥运会,悲愤、悲痛、欢喜、自信交织,深刻影响了国人对时代与世界的认知,形塑了民族的性格气质和未来想象。《若即若离》中的《小城有条冠军路》《和自己的城市一起沉醉》《今夜,我该为谁鼓掌》《奔走在灾区的老姚》《等你的笑容如花绽放》《如此美丽》《今日无喜,有的只是哀伤》等等篇什都是反映在奥运会或汶川地震背景下,个人及南通人民的情感脉动和实际行动。作者自己说书中“尤以2008年发表的文章最多”,这看似属于个人创作偶然,但回过来看,显然是个人对大时代的必然感应,无意中还将南通置于时代和世界之中去凝视和定位。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是塑造社会经济、文化样态、民族形象的重要时期。易晖认为需要重审90年代,这“既是一种历史的清理、历史的再认,也是一种自我的清理、自我的确认”。不难发现,《若即若离》中的《给对手一个拥抱》《夕阳·小屋·冰雪酒》《“队长奶奶”的嗓门》《心火》等等篇章,既是对“九十年代化”的记录,又都是2020年出版的《少年将要远行》中许多情节的原型。相隔十年,《少年将要远行》并非是对《若即若离》里文章的拼贴与连缀,而是一种基于后者对90年代的重审和再写。
《少年将要远行》讲述了小主人根喜进城上初中之前的乡村生活,表现了根喜在家庭经济破产后顽强向上、逐步独立的精神品质,塑造了景宽爷爷、大凤姨妈、高美丽等诚实善良的农民形象,折射出苏中农村的淳朴乡风和敦厚民风,传达出将传统道德文化融入新农村建设的呼吁。实际上,小说叙事如果只是为表达上述意涵已经是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了,但是作者的叙事意图显然不止于此。首先,小说透过录像厅、小虎队、苏芮、琼瑶、路遥等标志性符号,再现了90年代的社会文化氛围。主人公根喜多次提及路遥的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人生》。《人生》透过高加林在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抉择,折射出城乡曾经的天壤差距,及给乡村子弟人生命途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农村出身的作者对此中幽微情感和复杂滋味,无疑会有剀切的体会和辨证。其次,小说重现了亚运会、农民工进城、国企员工下岗、户籍改革等历史事件。以户籍改革来说,蒋德春凭借城市户口取到了高美丽,高美丽被公认为运气好,没想到不久蒋德春下岗沦为众人,户口的优势土崩瓦解;根喜父母当年要给他买个“城镇户口”,若干年之后根喜意识到了父母耗费真金白银的“荒唐”。这都是重新审视历史才有的发现和认知,而在当时“城镇户口”就是人们的“热爱和向往”,谁知道市场经济一日千里,城乡差距在日后逐步消弭,当然寄寓在重审历史之中的还有作者对时代进步的欢呼礼赞。
作者从农村走出,又长期工作于医院,对农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有着近距观察和切身感受。上世纪末,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不少家庭因为一人患病而陷入贫困。《若即若离》中的《莫名的悲哀》《两瓶酒》《医院里的唢呐声》等等篇章都是关于此类题材的书写和思考,展现了作者的仁心、温情,还有不时的无奈之情。《少年将要远行》里,大凤姨妈的女儿彩霞患病住院,全家陷入慌乱和焦虑,也使得根喜面临无依无靠的境地。幸好彩霞最终平安,小说在此宕开一笔描写根喜在医院看到的一幕:“临出医院大门时,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路牙上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他遭遇着怎样的悲伤,他无声的哭泣,让我在明晃晃的阳光里感觉到一丝寒意。”作者将成人具有的无奈、无力的同情心和悲伤感赋予了少年根喜,无疑表明根喜已经长大,到了离乡远行的时刻了。根喜未来在面临人生困顿或社会危难时刻,必然会反刍少年时的记忆和感知。这里显然蕴含了作者的自我反顾和时代回望,及对“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前进的方向”的思考与回答。
总体而言,储成剑在《少年将要远行》中,从上世纪90年代留守儿童生活的“小处”着眼,重审了时代浪潮给农村与农民带来的冲击影响,重建了70后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意涵。阅读小说,儿童读者可以随着根喜一起成长获得了精神滋养,走过90年代的成人读者会经历了一场主体的重新确认。可以说,《少年将要远行》不只是一部儿童小说,更是从农村走出的70后的必读书。
(作者/吴学峰)